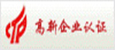您當前位置:首頁 > 版權注冊 > 行業新聞 > 探討我國著作權法中的報刊轉載法定許可制度(一)
探討我國著作權法中的報刊轉載法定許可制度(一)
日期:2021-11-11 11:18:25
點擊:
從立法角度來看,法定許可制度的理論基礎是法律明確規定,對此著作權人沒有保留和拒絕的余地。其更強調的是著作權人對于作品使用的“非自愿性”。換言之,只要法律明確作出規定,不論著作權人是否許可,他人都可以使用著作權人的作品。
報刊轉載法定許可制度的設立目的就是以權利的限制換取社會公共利益,防止權利人對于作品的過度保護而帶來的利益壟斷,從而有效促進作品的傳播。若賦予著作權人排除限制的權利,立法效果是有待商榷的。
王遷教授曾舉過一個“制作錄音制品法定許可”的例子。若音樂作品著作權人享有“聲明權”。即聲明作品未經許可,不得適用制作錄音制品的權利,以意定排除法定的限制。此種情況可能會帶來聲明權的濫用。對于意圖壟斷市場的唱片公司而言,可以通過增加許可費的形式,聯合音樂著作權人的聲明。以此達到阻止競爭對手使用相同作品的權利,并使得法定許可制度完全失效。
同理,如果允許報刊作品著作權人通過“聲明不許轉載”來排除對于作品權利的限制,那么報刊作品并不能得到有效傳播,公眾仍需要通過特定刊物獲取該作品,報刊行業仍可以做到對作品的壟斷,且只要事先與著作權人約定即可。與此并不能達到立法效果。
我國著作權法規定的權利限制中,出版教科書對于已發表作品的使用,以及錄音制作者對于合法錄音制品的使用,可以說與報刊轉載法定許可制度相同,都賦予了著作權人“聲明權”來排除作品權利的限制。
這意味著作品權利人能夠通過事先或事后聲明對抗法律所預期保護的社會公共利益。相反,我國著作權法第43條規定的廣播電視播放作品。以及《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第8條規定的網絡義務教育使用作品。上述兩個法律條文均沒有沒有賦予著作權人排除限制的權利,著作權人僅有請求支付報酬的權利。
這意味著目前我國法定許可制度存在著兩種類型,一類是法定許可制度,即通過法律明確規定限制著作權人權利,無論著作權人是否同意,作品均能夠被他人使用,且支付報酬”;另一類是準法定許可制度,即法律明確規定著作權人事先未聲明不允許使用的,即視為允許使用。我國報刊轉載法定許可制度與第二類相似。
律師總結
綜上,一方面我國報刊轉載法定許可制度通過限制著作權人的權利,來實現刊登于報刊中的新聞作品轉載;另一方面又賦予著作權人“聲明權”來排除法律規定對于作品轉載的限制。
由此可見,其立法邏輯是相互矛盾的,這并不利于新聞作品傳播。從當前立法效果來看,報刊轉載法定許可制度并不能有效保障報刊作品之間的有效傳播,著作權人仍享有對作品轉載的控制權。換言之,著作權人享有的“聲明”權導致作品創作者、傳播者以及使用者之間的權利關系存在矛盾。
因此,為解決傳統傳播形式而設立的報刊轉載法定許可制度,在媒體融合環境下仍保持著“準法定許可”狀態,其存在的必要性有待考究。
參考文獻
黃匯,《版權法上公共領域的衰落與興起》,《現代法學》,2010年第4期,第35頁。
王遷,《論“制作錄音制品法定許可”及在我國著作權法>中的重構》,《東方法學》2011 年第 6 期,第53頁。
呂炳斌,《網絡時代版權制度的變革與創新》,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頁。
《著作權法》第23條、第40條之規定。
推薦閱讀:
探討我國著作權法中的報刊轉載法定許可制度(一)
從立法角度來看,法定許可制度的理論基礎是法律明確規定,對此著作權人沒有保留和拒絕的余地。其更強調的是著作權人對于作品使用的“非自愿性”。換言之,只要法律明確作出規定,不論著作權人是否許可,他人都可以使用著作權人的作品。
報刊轉載法定許可制度的設立目的就是以權利的限制換取社會公共利益,防止權利人對于作品的過度保護而帶來的利益壟斷,從而有效促進作品的傳播。若賦予著作權人排除限制的權利,立法效果是有待商榷的。
王遷教授曾舉過一個“制作錄音制品法定許可”的例子。若音樂作品著作權人享有“聲明權”。即聲明作品未經許可,不得適用制作錄音制品的權利,以意定排除法定的限制。此種情況可能會帶來聲明權的濫用。對于意圖壟斷市場的唱片公司而言,可以通過增加許可費的形式,聯合音樂著作權人的聲明。以此達到阻止競爭對手使用相同作品的權利,并使得法定許可制度完全失效。
同理,如果允許報刊作品著作權人通過“聲明不許轉載”來排除對于作品權利的限制,那么報刊作品并不能得到有效傳播,公眾仍需要通過特定刊物獲取該作品,報刊行業仍可以做到對作品的壟斷,且只要事先與著作權人約定即可。與此并不能達到立法效果。
我國著作權法規定的權利限制中,出版教科書對于已發表作品的使用,以及錄音制作者對于合法錄音制品的使用,可以說與報刊轉載法定許可制度相同,都賦予了著作權人“聲明權”來排除作品權利的限制。
這意味著作品權利人能夠通過事先或事后聲明對抗法律所預期保護的社會公共利益。相反,我國著作權法第43條規定的廣播電視播放作品。以及《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第8條規定的網絡義務教育使用作品。上述兩個法律條文均沒有沒有賦予著作權人排除限制的權利,著作權人僅有請求支付報酬的權利。
這意味著目前我國法定許可制度存在著兩種類型,一類是法定許可制度,即通過法律明確規定限制著作權人權利,無論著作權人是否同意,作品均能夠被他人使用,且支付報酬”;另一類是準法定許可制度,即法律明確規定著作權人事先未聲明不允許使用的,即視為允許使用。我國報刊轉載法定許可制度與第二類相似。
律師總結
綜上,一方面我國報刊轉載法定許可制度通過限制著作權人的權利,來實現刊登于報刊中的新聞作品轉載;另一方面又賦予著作權人“聲明權”來排除法律規定對于作品轉載的限制。
由此可見,其立法邏輯是相互矛盾的,這并不利于新聞作品傳播。從當前立法效果來看,報刊轉載法定許可制度并不能有效保障報刊作品之間的有效傳播,著作權人仍享有對作品轉載的控制權。換言之,著作權人享有的“聲明”權導致作品創作者、傳播者以及使用者之間的權利關系存在矛盾。
因此,為解決傳統傳播形式而設立的報刊轉載法定許可制度,在媒體融合環境下仍保持著“準法定許可”狀態,其存在的必要性有待考究。
參考文獻
黃匯,《版權法上公共領域的衰落與興起》,《現代法學》,2010年第4期,第35頁。
王遷,《論“制作錄音制品法定許可”及在我國著作權法>中的重構》,《東方法學》2011 年第 6 期,第53頁。
呂炳斌,《網絡時代版權制度的變革與創新》,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頁。
《著作權法》第23條、第40條之規定。
推薦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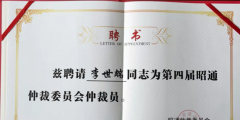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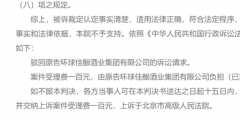





.png)
.png)
.png)